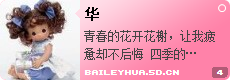这一袭白衣的俊秀男子,是如此的与众不同,人人见了我,都惊艳地恨不得多生千双眼睛,以多看几分我的风姿,他却微笑着睨一眼而掠过,停留在站在我身后的云白身上。云白是我的姐姐,我大胆问他:许相公,究竟朱纱有何不好?他的微笑如此迷人:朱纱你生得如此艳丽,天下名士皆闻名拜见,何须多我许夏至一个。我顿时泪起眼眸
西汉,汉武帝时的长安城。
春满楼宾客似锦,其中不泛王公贵族,据说其中气宇轩昂出手最为阔绰的那一位,是微服寻欢的当今天子。他们一掷千金,不过是为了博云白与我的欢颜一笑。春满楼是云白与我开的酒楼。宾客踏破门槛不是因为春满楼的酒菜,而是云白与我的绝世姿色。
云白与我,是姐妹。我们无亲无故,两个无依女子经营着这样一间酒楼,自然也有着风光之后旁人看不见的苦楚。我们何尝不想日日闲在深闺赏花操琴,可我们不得不如此。
女人每做一件事,都是为了情的冤孽。云白与我,又怎么逃得出?
茫茫人海中寻一个前世的有缘人谈何容易。为了遇见他,在人最多的地方开一间酒楼,总是一件机率大一些的容易差事。
他出现的这一天,微雨。
大早,宾客仍然如常。云白与我,隔着竹帘坐在楼廊享受温润清新的空气。
远处马蹄声响
原来是他。
他终于来了。在京城温润的微雨中翩然而至。他还是那样只爱白色。纯白色的骏马,纯白色的衣裳。
我轻轻对安坐在我身边波澜不惊的云白说:姐姐,你看你看,他还是爱纯白。他还是只爱你一人。
云白仍然没有表情,许久她才轻轻说:那又如何?
转眼间,俊秀的白衣男子已到楼下,他顺着楼下向上观望的人群的目光向我们看来,那是俊秀的一双眼,闪着星一般的光芒。这闪着星一般光芒的眼睛,只扫了我一眼,就落在神色淡然的云白身上,再也不愿意移开。
第二天,大雨
云白与我,闲坐后庭看雨打落花飞珠溅玉。云白与我,很少说话。几千年时光下来,我们早已不需要用说话才能作沟通,一个眼神,便能明了对方的心思。
丫头来报,说黄天公子与许夏至公子求见。
云白依旧清冷地看着大颗坠落的雨滴不说话。
我对丫头说:请他们进来吧。
黄天公子钟情与我,春满楼里无人不晓。客人多传他是当今天子。我知他底细。他不是天子,却是天子最得意的儿子。他常住春满楼,自是为了博我欢心。而我的心思,却是从来不在他身上的。
至于许夏至,就是那白衣白马的俊秀男子,我的冤家,云白的冤孽。对白色有着近乎执着的喜爱,就连这名字,五百年过去,也一字未改。就似他对云白,云白对他,我对他,一切未改。也是,情这一物,又怎么是说改就能改的呢?
黄天公子看到我时眼里的光芒,我自然懂得。但可惜,他却不是我炽热地想念的那个人。也好,趁这美妙的雨天,让他知晓我的心思。
纱儿,今日大雨,我知道你欢喜,喝些梅花露听雨,应该不错。
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也难得他屈尊降贵亲自捧一碗梅花露来讨我欢心。
我并不接那碧玉碗里晶莹的梅花露,我只看着他,轻轻地问了一句话,就让他捧着碧玉碗暗淡而去。
黄公子,今日你钟情于我,他日你便是天子,三宫六院,繁花万朵,你可能保证一生只恋我一人?
从此春满楼再无黄天公子踪影。
许夏至对云白的痴迷,却仍是隔世不改的。
包下了春满楼最好的客房,日日挖空心思想博云白一笑。
我依然是众星拱月的华丽,世人皆喜牡丹艳丽,又有几个能像许夏至公子那般只爱云白多愁不笑的清秀女子呢?
云白性子比我更淡,我红衣艳丽,多少还貌似可亲近。但云白不同,云白只喜欢站在我身后,不管遇着何事,别人欢喜或者忧伤愤怒,她都面色安然,不恼,当然也不笑。
所以没有人知道云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
用情至深的许夏至公子,自然也不知道。
但他至少知道要来问我。
初夏的阳光在繁树绿影的回廊间绰绰约约,白衣如水的男子在我面前轻轻地作揖,朱纱小姐。星一般闪亮的眼睛,剑一般飞削的眉,悬胆似的鼻梁高高
许公子。
朱纱小姐如此聪慧,想必也看出我对令姐情深一片,我有意与令姐共结连理,想送她一件小心意,只是不知她喜爱何物,望朱纱小姐你指点。
我抿嘴媚笑:是不是任何事,你都愿意为她做?
许夏至公子信誓旦旦:这是自然。
一个月后,官府下了公文,令春满楼后院方圆十里的百姓搬家,由江苏许公子代付安家费用。
整个京城议论纷纷,传言许公子富可敌国,竟买下了春满楼后院外方圆十里的土地,要在这寸土宝贵的京城最繁华之地建一处莲池。
大宅民房纷纷倒塌,蚂蚁一般的工匠们在大片的废墟上日夜工作,坑渐渐地挖出来了,水也慢慢地引来了。
这是多大的一个工程,在京城最繁华的街道上挖一个方圆十里的莲池。
云白看着那些劳作的人们,问我:又是你的主意?
我笑着回答:任何事,他都应还你,不是么?
你不应折腾他,不管他做什么,我心里都不再有他。云白说完,就回屋了,从此再不看日渐成景的十里莲池半眼。
是,是我对许夏至说:云白喜欢雨中的白色莲花。你若真想讨她欢心,就送她一个莲池吧。
许夏至想必比起前世那个贵公子,还要更富贵一些,竟然动用了官府的力量。
这一点那个号称对我情深的黄天黄公子来说,却又是更加不管不顾一些的。
即便黄天公子也如此为我又如何,我心里仍然没有他。
女人毕生最难忘记的,总不是那个对她最好的人,而是那个伤她最深的人。
转眼,一个夏天过去,新栽种的莲叶在秋天的京城瑟瑟,再转眼,枯黄暗淡地没入了水中。一场大雪,冬天便来了。春满楼的后院方圆十里,银白一片。
每年冬天,云白总是特别虚弱,几乎不能出屋,她背部有大片的旧伤,每年冬天让她蚀骨地疼痛。我抱了个暧炉,坐在她床前,给她读一段书。
云白的手,苍白而冰冷。房间里几乎已经温暖如春,可云白,仍然不能暖和起来。
二小姐,许公子说要来探望大小姐。丫头轻轻地掀了厚重门帘进来
我轻轻把云白的手放入被子里,说了两个字:不见。
冬天是云白,也是我都难以挨过的漫长时光。我们都怕冷,云白有旧伤。每年冬天她都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,我总怕她熬不过。即便她永远不会死去,可每年整整一冬的疼痛,试问有谁能一直承受?
清晨起,春满楼楼下门有立雪,扫雪的佣人过去推,倒下,原来是冻了一夜的许夏至许公子。
幸好,春满楼里住了一位名医,被救醒后的许公子第一句话是:请告诉我云白如何了?
但我仍是不愿意让他见云白。
许公子日渐憔悴。
这一冬,发生了好多事。
京城连日降大雪。
云白如往年重病不愈。
许公子相思成灾。
消失多日的黄公子再度光临春满楼。
自然是找我:纱儿,我这卷昭书,换你相许,如何?
金黄的缎子,朱红的玺印,是贬储昭书。
黄天公子说:没有你,我要天下又有什么欢喜?
他竟为我放弃了做天子。可他怎么能放弃呢?这个天下,注定就是他的,不是他说放弃就能放弃。
只是这是天机,自然不能现在告诉他。
只是纱儿,我不能为你也在京城建一个十里荷塘。我答应父亲,有生之年永不回皇宫。我们去温暖的南方,寻一处水乡,我亲自为你栽种每一株莲花,我们听雨赏荷,逍遥自在,好不好?
他所描画的未来,怎么不好,只是,再好又如何,不是我的未来,也不是他的未来。
我没有拒绝,也没有答应,只是吩咐下去:给黄公子备天字号客房。好生侍候着。
这凡间,有些人是天生命定,是平民,便永远平民,是天子,便永远做不成平民。
黄公子与住在隔壁养病的许公子,自然成为了好友。
据说许公子闯入云白房间去的当日,黄公子是这样对许公子说的:纱儿只是护姐心切,她总是如此,面恶心善。从不见大夫来为云白诊断,想必只是姑娘家怕冷。只是见一面,能如何?
他一句轻言,差点使云白丧命。许公子硬是冲过下人的阻拦,撞破门进入了云白的房间。风雪大作跟随他而入,可怜的正在用最后一丝力量忍耐疼痛与寒冷的云白,受了这一阵的风寒,就昏迷过去。我闻声而至,管不了许多,拂袖之间关上门窗并把许夏至打晕在地。
我于帐内试图把一些真气输给云白,但她始终绵绵无力不见醒来。
我命人把晕倒的许夏至扔出去:以后再不许接近云白的房间!
醒来后知晓云白因他莽撞,而病得更重的许夏至自然是悔不当初。出了坏主意的黄公子,甚至不惜出尔反尔,违反与父亲订下的约定,回宫去请来了御医。
但所有的大夫都只会摇头不说话。
我早知如此。
只是不肯承认事实。
我购买了京城里几乎所有的炭火,在春满楼周围日夜取暖,只希望这个冬天快快过去,温暖的春天快快到来,好让云白有醒来的希望。
黄公子回宫了。命人送来两块暧石,据说是天降陨石而成,炽热恒久不变,向来都是皇太后过冬用。
我知他是为了表达歉意。也知他与我,总算是缘尽于此。
说也奇怪,不知是春满楼炭火生得多的关系,或者是春天真的早到了,春满楼里的树竟然在寒冬十二月抽出了新芽。
许夏至许公子日日痴痴地站在云白房间的楼下,日落日出,云卷云舒,风雪雨水,似皆与他无关。他心里,只记挂着云白。
靠着黄公子送来的两颗炽热的暧石,春满楼的树都抽了枝,眼见轻绿了整个庭院。而奄奄一息的云白,终于悠悠醒转。
她最终见了形消骨立的许夏至。见了她,许夏至的眼睛终于星光熣灿。
云白只对他说了一句话:若这十里荷塘今年开的莲花,全数是白色,没有一朵是红色,就算我们有缘。就算是只有一朵红色,我与你,就注定各自天涯。
许夏至信心满满地答他:我知你只喜欢白色莲花,所以我特地亲自去选种,到了夏天,你必会看到十里白莲。
许夏至公子含笑下楼去,我把暧炉放在云白手里,说:你何必骗他?
云白翻身趴在床上,悠悠说:我不是骗他,我要他知道,这劫数,是命定。
我轻轻掀开她的衣裳,她背部触目惊心,粉红色的血肉模糊,仿佛什么东西,生生磨去了她的皮肤,让她受这切肤之痛。我轻轻地把一种透明的药膏涂抹其上,我知她痛极。可是没有这药膏,她会更痛。这伤口与她与生俱来,从未离开过她,所以她每年冬天都须冬眠。
我没有再说话。
别人的白莲塘里可能会一色白。但云白的白莲塘里必定会开一朵红莲。
白莲是她,红莲是我。云白没有我,根本不能生存。
云白与我,是佛堂前荷塘里的两枝莲花。我朱红,禅师给我起名朱纱。云白纯白,禅师赐她云白为名。
你定不知几千年的修炼何其苦,所以才责怪我们,好好做一株佛前莲花岂不更好,何须幻化成人受这人间情劫。
见到云白之前,我寂寞地在佛堂前开了一千年,倒也自在。而云白,在成为佛堂前的白莲之前,她作为一颗古莲子,在一棵大树下,已经沉睡了三千年。
她寂寞,而安静。她希望遇着一个发现她的人,她会为他绽放她蕴藏了三千年的美丽。
终于有一天,一个小男孩在玩耍时发现了她,他好奇地把她捡起,时光的力量把她的外壳变得硬如磐石,此刻的她,一点不美丽。男孩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一颗什么东西。他用牙咬她,用脚踩她,用石头砸她,她疼痛不已,但是坚硬的壳最终还中保护了她。
小男孩最终开始坐在河边用卵石磨她,一点一点的磨。
云白痛彻心肺,可她不能说话,她不能对他说请你不要再磨了。她什么也不能说。她只能痛着,看着这个发现了她的俊秀男孩在用力地磨她的壳。
千年的时光铸就的硬壳是磨不掉的,但是一滴泪水最终磨掉了云白的壳。
因为发现磨了那么久,这种子竟然丝毫无损,小男孩为她流下了一滴眼泪。
于是为着这滴眼泪,为着他发现了她,云白尽力地把自己变薄变软,快快打开,给他看看自己那颗柔软的心。
终于被磨开的那一刻,云白的背部切骨地疼痛,可她还是微笑了,以为自己可以和小男孩永远相伴。只要他种下自己,她会为他开最美丽的纯白莲花。
可是看见里面饱满的果仁,终于弄明白,这只不过是一颗种子。
他于是丢弃了他,继续玩儿去了。
云白在阳光里无泪地哭泣,无情的粗沙磨砺着她的心,让她疼痛难当。她想,她将永远没有开放的机会。就在她将死时,路过的禅师捡起了她,并且把她种进了佛堂前的莲池。
我第一次见云白,她就是这样的奄奄一息。她甚至不想生长,不想发芽,当然更不想开花。可千年来我那么寂寞,我需要她的陪伴,我用我千年来吸收的月光精华覆盖了她的伤口。云白没有发芽,也没有死。整整十五年,她一直在沉睡。一直到有一天,一个骑着白马的俊秀公子来拜访禅师,人们称他许公子。他见了我,说:呀,这红莲开得甚好。
因这一句话,我芳心从此暗许与他。而云白,因他而醒了。她发芽,生长,我知她想看看那个说话的公子,因为他就是当年就是发现了她,也伤了她的那个小男孩。
第二年夏天,云白真的开了。她比月光更加皎洁美丽,与我一朱红一纯白交相辉映,来拜访禅师的人们争相盛传我们的美丽。
许公子终于也来了,带着他温婉的妻子,他说:你看,多美,我更喜欢白莲多些。
因这一句话,我终注定芳心是空许无望。
许公子求禅师将云白割爱,送与他带回府中。禅师说:你是与白莲有缘,只是,因一些过往,白莲离了红莲,是不能独生的。
我用月光精华救了云白,云白从此便要依附我才能生存。
可是云白那颗被磨伤的心,就像她背上永远好不了的伤口,时刻提醒她,她再也不愿意把心交与许公子,甚至是,任何一个男子。
禅师仙去前,对我与云白说:你们到人间去吧,直至云白忘记了恨,而朱纱忘记了爱为止。
于是云白与我,便作姐妹辗转人间,世世与许公子相逢。他伤了她,也欠了她,她始终对他有恨,我始终爱而不得。
夏天终于到来,十里莲塘的白莲齐齐开放,成了京城的第一景观,十里纯白的正中央,有一朵红莲,朱砂似的红,映日间愈加娇艳。
是夜,月黑风高多变故,京城最繁华的酒楼春满楼火蚀,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清晨,灰黑的废墟中有一白衣男子,跪地长哭。
据说,春满楼的老板,那一红一白的美丽姐妹一夜间葬身火海。
城外南去的一辆马车里,云白问我:下一世,我们又在哪里遇见他?
我说:等我们不恨了,也不爱了,我们就合做一朵莲花吧。我们不做红莲,也不做白莲,我们一起,做一朵粉红莲,好不好?
云白终于微微地笑了,她轻轻地说:好。
1953年3月,在日本千叶县东京大学厚生农场地下7米的青泥层中,一艘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船上被发现。船中有两粒莲花种子,经日本资深植物学家大贺一郎博士的精心培育开花,花色娇艳粉红,这株显示生命奇迹的莲花,被命名为大贺莲,年年粉红娇艳花开正好。